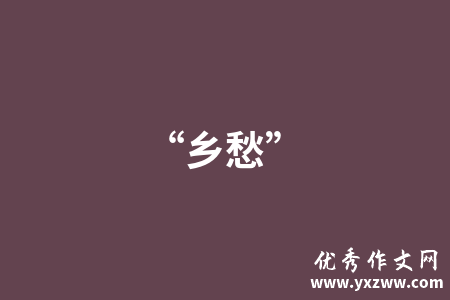
(一)
我时常怀念起自己以前的状态。
紫薇花漫天漫地地开,窗外光影摇移,无数重,看不真切。我盯着一只蝴蝶翩翩落下,那么美的一双翅,扑扑闪闪,让我回忆般看破了它孩子时破茧的模样,破开,外面是新生。
那一刻,摸到自己羊水般软糯稠腻的童年,像打落了一本看不清皮肤的大开本童话书。
大开本“啪”地夹起来时,夹出一阵风,掀开女孩子的刘海儿。她的脑袋像团子粘着锡纸,贴上厚厚的书封。我看到她蜷着白生生的指头,在逗引着阳光绕圈儿,吧咂吧咂嘴,眯着眼,低眉浅笑。午后的阳光永远热烈,泼泼洒洒,在教室空旷的地面上长出异艳的鳞片。走进阳光去,每个人都花花的,那些安静地游逛的同学,迎着一张茸茸的面孔,谁也不说话。
时光漫漫地淌过鬓边,淌过软香的熟米般的发,那个女孩子,脑后束着长长的马尾。不读格林童话,也不翻莎士比亚,头就一本数学书枕在桌上,教室里人声鼎沸,她隐约听到粉笔在并不光滑的黑板上“喀、喀”地响动。
“哎,哎。”
有人推了她一下,她迅直起腰来:“嗯?”
他把一件厚重的东西在手中掂了掂,头垂了好一会儿,才说:“给你看本书。”
《狼王梦》?
她接受了。
风漫书页,陆陆续续录进脑海里。随时可能飘浮起的断句残篇,在她脑海里闪过一幕一幕画面。从此,他转身走向她时,携来的满袖气息,让她瞬间望穿了绵延千里的大草原,大雪山终古不化,拔起阵阵延宕的松香,麝鹿扑腾,群狼奔窜。而后他渐行渐远,只留下一个描过似的背影,松香飘忽着从她心里过去,消却了。
从此,记了许多人的生日,而后悄悄在寿星们的抽屉里,塞上一本书,一张简短的纸条飞上书面,絮絮叨叨都是她的碎碎念念,像一只只扑飞的蝴蝶,停在她给予给那许多人的灵动嗅觉上。
她是拿出了那一本本书,铁柜的阀门“喀喀”地抽开,又锁上,笔墨涮涮地飞,飞上她粉玫瑰色的便签;她抱着一摞书潜进教室后门去,阳光铺天盖地地在石地板上滋长,那些书,塞给每一张沐在阳光下的花花的身影。他们一众转了身来,低了头微笑,茸茸的面孔,每一张都望不真切。
最后的大开本童话书递出去的一刻,她的眼眶,突然很酸;心里被什么碰得有些疼痛,像夏秋之际即将休眠的空调在滴水,冷冰冰,滴,滴答,滴,滴答。
啊,再见,再见!一去不复返的童年!
(二)
从冗杂的梦里苏醒,她咬着笔杆,只手扶着太阳穴,眼神停在高高叠起的作业本上,她突然很苦恼,目光沉默地扫过满当当的教室,满当当的沉默。
她的手窜进包里,漫无边际地翻找着课本,手指却撞上一件硬邦邦的东西。用些力拖拉着,拽了出来。噢,一本书。眼神定了定,书皮上的字凝固不动了,噢。脑海里用力地挣扎了许久,她什么时候放进包里的诗集呢?
开学那天起,她为自己准备了一本诗,她说:“你每天读一首罢。”
从什么时候开始,她读得这么乏乏的呢;她摸着书的表皮,教室里吊着明亮的灯,放射着一束又一束白色光线,把书照得明明白白。她吊起疲惫的眼皮,把额头靠上了书封。
这么久没读书了。
略略剥开了封皮,微黄的纸页上泛着诗行,她的目光只一秒,被一段话吸去。
“去寻找那些,曾出现在梦境中的山峦与田野吧。
趁阳光正好,
趁微风不燥……”
诗集光饱饱的,被她整个儿抱在怀里,她摸了摸自己白纸一样,没有活力的脸庞,若有所思。小时候,诗集闻起来,是一米长的阳光,是绕过辫梢的风,是远去的山峦,是金色的田野。
凑近了闻,那些气息混在人群里很淡很淡,却要从她记忆里,抱出一个美丽的孪生儿。
好像那一天,雪松香漫过鼻尖,阳光铺天盖地,紫微花漫过窗台;她抬头望,推开了窗,探头向窗外的远方。有湿湿的东西,环着她的腮流下去,——远方,远方。远方!
曾几何时,我坐在教室笔耕不辍,一声不响。头顶上吊着的灯管吱啦作响,喷射人工造作的光束。彼时我在想,我原来没有那么充足的时间,没有供以闲暇的心情,没有抬起头瞄一眼晚霞,于是漫天黑夜里陷入无穷无尽的疲惫。
我盯着手上沾着的露水一样的泪珠,问自己:“这是乡愁吗?”
其实我早就不是以前那个浪漫无忧的孩子了。颠扑不破的羊水里,装着我的童年,推开窗往外看时就像蝴蝶破茧,世界还是原来的样子,可不再是我的我,眼里却闪动着泪光,那是我对自己的乡愁。